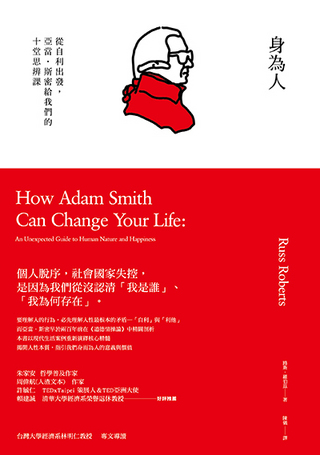
文/林明仁(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凱因斯曾說:「經濟學家與政治、哲學家理念的影響力,不論對錯威力,都比一般人所能瞭解的還要大,統治者通常只是某些已故經濟學家在思想上的奴隸而已。」從這個標準來看,《國富論》對近二百年來世界體系運行與資源分配方式觀點爭論的重要性,恐怕無書能出其右。祖師爺分析技巧與同時代的學者相較,或許不是最突出的,但是《國富論》就像是一個巨大的經濟思想水壩,之前所有對經濟體系如何運作的想法,都被匯流至此,而之後所有的觀點,也都從此而出。舉例來說,二十世紀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的公共選擇理論(publicchoice theory),或者是史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的管制理論(theory ofregulation),都可從《國富論》找到對應之處。而他最重要的貢獻,即是第一位提出以自利心(self-interest)為出發點,論證在競爭市場的前提之下,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將會讓整個社會的福利達到最大的「市場機能」說。這個偉大的洞見,也讓後世尊稱他為經濟學之父。
斯密於一七二三年出生於愛丁堡近郊的一個小鎮克爾卡迪(Kirkcaldy),是一名律師的遺腹子,從小身體不算健康,但是對書本有極大的愛好。十四歲時他到格拉斯哥大學研讀道德哲學、數學與政治經濟學,並在十七歲獲得牛津大學的全額獎學金。有趣的是,當年的牛津大學教授是以「假裝教書都不願意」出名,根本就不上課!(所以斯密曾主張,大學教授的薪水應該跟他所教的學生人數成正比)一個例子是:在該校一場辯論會上的四位參賽者,全場沒有一個人講出任何一句話;大家都在滑手機(誤)閱讀流行小說(正)!
這樣的環境對斯密來說,可能反倒是如魚得水。在六年內,他讀遍「他認為重要」的書籍,而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恐怕非日後好友大衛.休謨的巨著《人性論》莫屬。事實上,斯密還曾因房裡藏有這本主張「道德與政治的基礎是自利心」的著作,差點被牛津開除呢!二十八歲那年,斯密受聘為格拉斯哥大學邏輯學與道德哲學教授的職位。八年之後,他將其上課講義編輯出版,命名為《道德情操論》,本書一出立刻「倫敦紙貴」,也讓他擠進英國頂尖哲學家排行榜。
經濟學祖師爺化身心靈雞湯導師?
《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都已經進入當代的經典巨著之林。但諷刺的是,經典即是「大家都聽過,但都沒讀過」的書。特別對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來說,十八世紀那種一個句子有四十二個單字的古文體,的確是太詰屈聱牙,難以下嚥。在本書中,作者簡潔有力地介紹了《道德情操論》的基本論點,並且舉出非常多現代生活中的例子加以詮釋。這讓一般大眾,甚至是經濟學系的科班生認識斯密的成本,大大地下降了。當然,讀者也不可忘記自己是走在作者精心安排的路徑上被導覽著的。不過,世間事皆有取捨(trade off),不是嗎?
本書共分十章,作者首先介紹了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破題的大哉問:「為什麼一個自私的人,在本性上還是會堅持某些節操,…….並認定旁人的快樂對他是重要的?」斯密接著也說:「同情心(sympathy),意即感受他人的苦痛的能力就是這節操的一種。」
但斯密卻以一個尖銳的設問繼續討論這個問題,他說:「當我們知道自己即將失去小指頭,心裡的感覺一定比聽到遠方有大量陌生人死亡的感覺糟很多!」但是若有選擇,斯密追問:「是否有人會為了保全自己的小指頭而讓遠方素未謀面的人大量死去?」畢竟「同情仁慈的力量,再怎樣強大也無法與內心的自利衝動相抗衡!」
上述的答案,顯然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否定的。雖然人類天性齷齪,但社會卻也沒有到達像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言,「每個人都是每個人的敵人(every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 的自然戰爭狀態(state of nature)。不過與霍布斯不同的是,史密斯認為問題的答案並不在於《利維坦》(Leviathan)下的社會契約,而是因為我們內心深處有一個無私的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的緣故。自利的自己所做出的決定,必然會被無私的旁觀者加以審視,它會時時對你諄諄教誨,讓你知道「慷慨的合宜與不公不義的醜惡」。無私的旁觀者為你自己設下了一個道德標準,如果你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傷害人,那你將永遠受它憎恨(也稱道德良知的譴責)。不可諱言的,當面對的決定愈困難,內心小劇場中,自利心與無私旁觀者的對戰也就愈激烈。作者以《悲慘世界》尚萬強所面對的道德難題為設定:「我是誰?(who am I?)我真的要讓一個無辜的人代我入獄?」當然在一陣激烈的歌唱對話後,尚萬強終於作出了無私的旁觀者讚許的決定,大聲說出:「Who amI? Who am I? I am Jean Valjean!」
喬安.羅賓遜(Joan Robinson)在其《經濟哲學》(Economic Philosophy)一書中,也對同情抑制自利的成效表示懷疑。她認為這是「as far as it goes, and doesnot cover the whole ground.」除了母親保護小孩外,「利他在其他情況下都不太可靠」。因此道德感就成了最重要門閥,而無私的旁觀者就是此一機制中那個提供判準的法官。
從無私的旁觀者這個概念展開,作者從閱讀《道德情操論》的過程中提煉心得, 並與他自己的生活經驗對話,畢竟道德的確也就是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準則。舉例來說,第二章就提到隨時把無私的旁觀者放在心上,「不但有助於了解你自己,也有助於你與現實生活中實際的旁觀者互動良好。」第三章則討論了斯密所認為的快樂的來源。他提到:「有什麼比受人喜愛,且知道自己本該受人喜愛更快樂?」作者接著問,當我們得到不應得的恭維時,我們會快樂嗎?還是我們能誠實面對自己?拒絕不應得的恭維或許不會太難,那拒絕自己對自己的讚美呢?的確,如果沒有無私的旁觀者,我們要如何能對自己誠實呢?
接著下來的第三到第七章中,作者從個體角度討論要如何誠實面對自己,因為有時自利心也會愚弄無私的旁觀者,並將其與現代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結果結合起來;他也討論到怎樣才能受人喜愛,成為一個可愛的人;精巧但沒有實質用處的小玩意如何讓我們玩物喪志;過分的激情對人生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為何審慎、正義和仁慈是最重要的美德等。第八章開始,作者說明了在一個由同時受無私旁觀者與自利心驅使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中,自發性的秩序會如何被創造出來,以及如何避免如「執著體系的領袖」般,相信所有人都如同棋盤上的棋子,任領袖擺佈,完全忽略棋子自然移動的力量。忽略了體系內行動者的反饋,經常是導致政策失敗的主要原因。此即經濟學家所謂的「始料未及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在現實世界屢見不鮮。最後一章則討論《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之間的異同。相對於前七章,這三章則比較像是從總體的角度去思考個人道德互動與整體社會之間的關聯。
作者在書中加入了許多現代社會的例子與他自己的經驗,替這本書增加了很多可讀性。在此我就不再爆雷,以便掃了讀者閱讀的興致。不過對於最後一章的內容,我想在此作些討論。
《國富論》vs《道德情操論》:雙重人格下的產物?
沒有讀過道德情操論的中文讀者,可能會感到困惑:亞當.斯密不是資本主義、自利心的提倡者?(此時請讀者腦海中浮現《華爾街之狼》中李奧納多那張貪婪的帥臉)怎麼會提倡道德情操?我在台大經濟學原理課程的教學評鑑,也有學生怒吼:「不要每天強調斯密的《國富論》和市場機能!他也是《道德情操論》的作者,強調道德很重,要多讀一點書!」
然而,只要看本書的英文書名:《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就可以瞭解這不是一本教導大家要有道德,不要自私的書;而是試圖建構一個探討道德起源與演化理論架構的著作(所以才有the theory 這兩個字)!
不過即便在哲學與科學層次的討論上,斯密(表面看來)的雙面性仍然是令後世學者相當困惑的:在《道德情操論》裡那個有同情心,能以無私旁觀者角度思考的人,跟在《國富論》中自利的那個人,怎麼可能是同一個?一個一生只寫出兩本著作,但都對人類社會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的人,怎麼會將兩本書奠基在如此不同的假設上?此即德國哲學家所謂的「亞當.斯密的問題(Das Adam Smith’sProblem)」。
斯密本人對這件事倒是沒有任何說明:他在《國富論》中從未提及《道德情操論》,更遑論自己是該書作者這個事實,他從未討論過兩本書之間的關聯,也因此留給後世學者許多發揮與爭論的空間。
舉例來說,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我們可以將《國富論》裡的自利假設,看成是互利市場交換所需的最小要件,而《道德情操論》則是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標準如何產生,並被鑲嵌進我們的行準則中。然而,沈恩(Amartya Sen)就認為:斯密的《國富論》只狹隘地聚焦在單純的交換上,並未討論生產與分配的問題(這一點我倒是不同意。生產也是一種交換,而產出的分配則是生產這個交換會不會發生的最重要條件)。而如果沒有以道德為基礎所產生的信任,自利對交換與福利增加的好處也會大打折扣。麥克隆斯基(Deirdre McCloskey)甚至說:「斯密是西方智識史最後一個道德哲學家!」
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則從一個二分法的角度切入,他認為斯密在這個問題上採取的是一個歷史的角度:在《道德情操論》中所提及,每個人都相互熟識的小社會中,道德與利他的確就足以成為維繫村莊秩序的重要力量;然而在如倫敦、紐約這種舉目皆是陌生人的資本主義下大都會中,只靠利他是無法存活的,因此人們行為的動機就會轉變成利己,這其實也代表斯密瞭解美德的極限。在幾乎都是陌生人的市場體系中與人互動時,無私的旁觀者也會同意將自利作為首要考量。
然而,假設這兩本書是完全對立的,難道就沒有問題嗎?有關這個亞當.斯密問題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來看待。首先,斯密在《道德情操論》裡就已經認識到,若天真的以為行為者會完全遵照制度變化行事,不考慮他們的偏好反應,是終將會失敗的,此即經濟學家最強調的「始料未及的後果」。 而此一後果,即是在個人依外在環境作決策並在市場互動的結果,這與《國富論》以來,經濟學家所謂市場均衡的概念是一致的。
再者,如同他的好友休謨一樣,史密斯對為什麼看似無人計畫的人際複雜互動,最後卻會產生井然有序的結果(即海耶克所謂「自發性的秩序」)的現象感到非常有興趣。而就如本書作者所言:斯密對這個現象最強而有力的描述,不是出現在《國富論》,而在《道德情操論》。當斯密談到社會的道德標準是如何決定時,他回答:「是由所有人決定的。」每一次的互動,雖然看似渺小,卻也都對道德標準產生滴水穿石的影響,「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不僅發生在商品與勞務的交易上,也發生在道德標準的市場均衡形成上。
最後,斯密是一個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不管是《道德情操論》或《國富論》,他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從個人行為動機的假設開始,去理解人們在商品交易或情感道德互動的過程,並且據此去推論整個社會最後可能達到的結果,以及此一結果是否能讓社會更加美好;換句話說,斯密在這兩本書中,討論的都是人類實際的行為,而非理想中的行為。只是,國富論聚焦在市場交易的財貨(marketgood);《道德情操論》則是討論非市場財(nonmarket good)。兩者都是透過「看不見的手」運作的。當蓋瑞.貝克(Gary Becker)告訴我們,經濟學分析應用到非市場財一點問題也沒有的時候,「亞當.斯密的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
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斯密的思想並無歧異,不論是在分析方法或是對人類行為動機的看法,《國富論》都是《道德情操論》很自然的邏輯性延伸。布勞格(MarkBlaug)曾說過:「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沒讀過《道德情操論》,那些讀過的人則會發現該書與《國富論》『表面上』是不一致的(superficially inconsistent)。」他也提到,最近格拉斯哥大學編輯的《Complete work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Smith》讓這個難解的爭論露出了一線曙光。布勞格認為,他在完成《國富論》後回頭繼續修訂《道德情操論》,應該是在構思一個更完整的社會科學架構,只是他沒有時間完成。我們不妨把自己提到像斯密一樣的高度,成為經濟體系運行的無私的旁觀者,笑看眾生的名利船隻,庸庸碌碌的奔波。我們會發現,這看似無規劃的自利競爭,不但給百姓帶來莫大的福祉,也同時產生道德來節制人們的行為!就如同海爾.布魯諾(Robert L. Heilbroner)在他的《俗世哲學家》(The WorldlyPhilosophers)一書中所言:「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寫道:『這個世界辛苦奔忙,追求財富詮釋與卓越,目的是什麼?』《國富論》提供了答案:『對所有財富榮譽的追求,都有助於百姓的福祉,終於能得到正當的理由。』」
亞當.斯密在一七九零年過世,享年六十七歲,不起眼的墓碑上寫著:
《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的作者,
亞當.斯密長眠於此,
生於一七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卒於一七九零年七月十七日
Here are deposited the remains of ADAM SMITH.
Author of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nd Wealth of Nations:
He was born 5th June, 1725, and died 17th July, 1790.
短短三行的墓誌銘,宣告此地長眠的乃是經濟學之父,還有哪一個人能用兩本書的篇幅,洞察人類行為的前因與後果,影響世界長達數百年之久?
●本文摘自臉譜出版《身為人:從自利出發,亞當.斯密給我們的十堂思辨課》